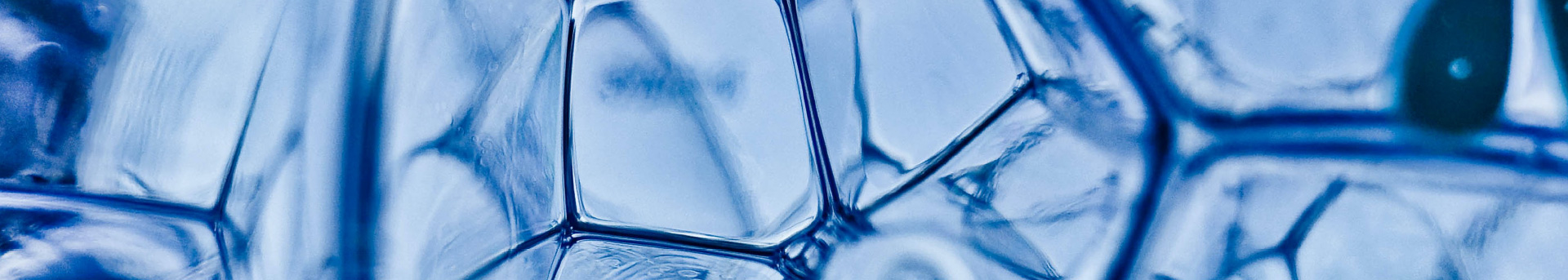

引言
202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发布,并于202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司法解释》将替代2012年5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解释》”)。
另一方面,《司法解释》对个别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了回应。根据《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项,如被告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的标准并符合其规定的其他条件,则纵向垄断协议可能会被免予法律责任。实际上,这一规定与《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相衔接,以便将来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出台具体适用标准后,根据《司法解释》的该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适用。
【趋势解读及实务启示】
二、减轻原告举证负担,实务影响利弊并存
● 特定情形免证相关市场和市场支配地位。就相关市场界定而言,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了原告有直接证据则不再对相关市场界定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的三种情形,第四款则明确了原告可以不对相关市场界定提供证据的情形。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面,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规定相关直接经济证据和被告的自我宣传证据可以初步证明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在过往的反垄断诉讼实践中,原告胜诉率很低,几乎所有原告败诉的案件均与证据不足有关。[4]数据显示,自2010-2019年,在309起垄断纠纷诉讼中,超过70%的案件中原告败诉;其中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案由的诉讼占比超过八成,这些案件中的原告败诉率接近90%,主要因为原告难以举证“界定相关市场”这一基础性因素。[5]可以说,“举证难、证明难”一直是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突出瓶颈。
通过上述诸多条款和措施,《司法解释》将有力地减轻原告举证负担,这将一定程度上降低发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门槛、提高当事人寻求反垄断司法救济的积极性。对于企业而言,这带来的影响可能具有双重性:既便利了企业运用反垄断诉讼的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如在反垄断方面不合规,面临其他方(比如竞争对手、消费者、上下游合作方等)发起反垄断诉讼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司法解释》明确企业对外宣传的信息可以成为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初步证据。这意味着,企业为市场宣传、业务开拓而对外发出的有关自身市场地位的内容,在“对簿公堂”时可能成为不利证据。因此,企业在发布对外宣传文案、新闻、广告等内容时,如涉及企业市场或产品等信息,建议也从反垄断合规工作的角度进行审核,应在客观评估自身市场地位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描述和宣传。
三、纵深推进民生反垄断,回应数字经济与药品热点
● 对数字经济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出规定。比如,第三十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市场份额计算及市场支配地位判断的考虑因素。此外,第四十二条还对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反垄断法》与《电子商务法》选择适用作了指引性规定。
在执法层面,此前我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已通过相关指引、文章等多种渠道,多次强调对数字经济进行“常态化监管”:注重兼顾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以促进其健康发展为目标进行常态化监管。《司法解释》从司法层面提出数字经济相关规则,既是对过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探索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因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新变化的垄断行为的回应,又是为了与未来一段时间数字经济“常态化监管”有机结合。
数字经济领域的经营者,由于其面向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的多边属性,再加上其业务与民生息息相关,因此任何个人消费者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均有可能在社会舆论层面发酵,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乃至监管机关的问询与调查。因此,在《司法解释》强化了反垄断“多方共治”属性和降低原告举证负担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企业更应结合《司法解释》最新规定,充分考虑自身的特殊性,对业务和运营开展审慎的反垄断合规,重视来自个人与第三方的反垄断诉讼,加强反垄断合规工作的“系统性”。
《司法解释》第二十条正式明确了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是否构成垄断协议的认定规则。如(1)专利权人给予或承诺给予仿制药申请人明显不合理的金钱等利益补偿,且(2)仿制药申请人承诺不质疑被仿制药专利权的有效性或者承诺延迟仿制药的上市,则可能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横向垄断协议。但被告可以通过证明前述利益补偿系为弥补被仿制药专利相关纠纷解决成本或其他正当理由来抗辩。
《司法解释》第二十条充分体现了我国反垄断司法实践的经验凝练以及对医药行业热点的及时回应。反向支付协议最早源自美国专利链接制度。通过2021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年修正),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也首次在我国落地,一定程度为反向支付协议及相关纠纷的出现提供了“土壤”。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对阿斯利康诉奥赛康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6]作出裁定时,首次对“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进行反垄断初步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该类协议的安排一般较为特殊,有构成垄断协议的风险,而其中的核心判断标准在于所涉协议是否涉嫌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
此外,在我国当前医药行业受到反垄断高度关注的背景下,《司法解释》从司法层面对药品行业热点作出回应,也再次反映了我国对保障民生的决心和投入。特别是,在执法层面,当前医药行业已呈现高压态势。在此之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多次在讲话和发言中强调了对医药垄断问题的关注,并且正在研究制定《关于药品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自2019年到2023年间,反垄断执法机关办结所有120件垄断协议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医药行业案件占比超过30%。
在这样的趋势下,医药企业加强反垄断合规工作已刻不容缓。而对于原研药企业和仿制药企业来说,应对和解协议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如确有必要签署相关和解协议,应事先进行全面的反垄断合规评估,确保有充分的正当理由并可有效举证。
四、经济分析引入反垄断司法规则,反垄断诉讼更趋专业性
《司法解释》融入了不少经济学要素,充分体现了反垄断诉讼朝向专业性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第十一条指引当事人可以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申请经济学专家出庭或出具经济分析意见,第二十九条专门将“经济学知识”这一概念引入反垄断司法规则的范畴。再如,《司法解释》还直接引用了网络效应、规模效应、范围效应、锁定效应等经济学概念。此外,《司法解释》对不少实体问题的分析思路,也充分体现了经济分析的重要性,如第十五条第二款提及利用假定垄断者测试界定相关市场,以及纵向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以及计算垄断行为受到的损失也离不开经济分析。
作为法学与经济学交叉的反垄断领域,经济分析在执法和司法中一直很重要。在当前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经济学家等专家证人/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比如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宣判的稀土反垄断诉讼案件中,原告和被告均聘请了经济学专家、出具经济学分析报告。此次《司法解释》实质性地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反垄断案件的审理,也是在与国际主流作法接轨的体现。
企业在日常运营和开展特定业务时,特别是涉及市场份额较高的领域,也可考虑提前将经济学分析纳入合规性评估的流程中。在反垄断诉讼更趋专业化的背景之下,企业在应对反垄断诉讼时,如能充分利用经济分析,或许可以就特定行为的竞争影响提供更有利的主张或抗辩。
Beijing ICP No. 05019364-1 Beijing Public Network Security 110105011258